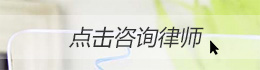
-
夫妻一方约定将个人所有的房屋与另一方共有,但没有办理房产加名登记,赠与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吗? 2021-12-27 09:51:03 李丽霞
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全部赠与另一方,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民法典》关于赠与一章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
一方婚前付首付,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的房产,应当如何分割 2021-12-27 09:49:44 罗京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离婚诉讼过错财产分割案所涉法律问题的辩析
来源:离婚律师网 作者:未知 时间:2016-11-22 点击数:29

成都重婚罪律师:沈辉
一、案情
王女士与张某婚后育一子。因张某与婚外异性有染,双方从2000年11月起分居。期间张某与婚外某异性C某在同居处受接举报的公安机关查处,此后C某又在同处被其夫和王女士堵获。不久张某向王女士提起离婚之诉。王女士应诉同意离婚并要求:张某就其过错行为向其赔偿5万元,补偿双方分居期间的子女抚养费,并以现金给付其应得的夫妻共同开办的公司资产折价款。
二、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认定张某与其他异性关系不正当,致夫妻感情破裂,判准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双方婚后财产的分割作出判决,其中以股权分割方式对双方所办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处理。同时该院以张某的过错未达到与婚外异性同居的程度,以及本案所涉公司内部资产的清算及债权债务的负担应由双方另案处理为由,对王女士向张某提出的损害赔偿、给付双方分居期间子女抚养费,以及以现金方式支付其应得的公司资产折价款的诉求均未采纳。
二审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部分判决事项,其中认定张某的行为已构成与婚外异性同居,判令其向王女士赔偿3万元;认为公司应由张某继续经营为宜,判决张某向王女士支付其应得的公司资产折价款6万元;认为王女士主张双方分居期间的子女抚养费证据不足,但判令张某应从一审判决宣判之月起,按月履行给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
三、分析
本案发生在新婚姻法颁布不久,该案的审理能否体现新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引起有关妇联组织的关注,新闻媒体予以跟踪报导。笔者作为王女士的诉讼代理人现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如下分析,并据此阐述无过错方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对过错方过错行为证据获取的立法缺失。
新婚姻法第四条以倡导性规范规定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第四十六条以救助性规范赋予了无过错方享有对过错方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其中“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系无过错方可行使此权利的事由之一。由此向社会彰示了现行立法的价值取向,即惩罚有违夫妻间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保护由此遭受损害的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据以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应该说这一立法意图是顺民心得民意的。但是根据诉讼规则,在涉及一方有过错的离婚案中,无过错方权益能否得到现实的保护,现行立法的上述价值取向能否得以有效的实现,完全取决于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行为能否获得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由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涉及私生活领域,行为人大多数背着无过错方而为的,无过错方作为个体以自助的方式难就此取得有效的证据,因而难以实现法律赋予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案例中的王女士幸有公安机关查获的证据,否则别说张某与婚外异性同居的事实难以认定,即使对其与婚外异性存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事实的确认都有问题,如此王女士损害赔偿请示求权的最终实现根本无从谈起。此类大量的个案表明在立法向社会公开彰示其惩罚过错方的价值取向的同时,立法者就应实事求是地解决无过错方对过错方过错行为取证难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现行立法对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立法上的缺失,既没有规定无过错方合法取证的有效方式,更没有规定无过错方向社会求助取证的途径。一个时期以来无过错方“捉奸”取证呈蔓延之势,由此引发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常引发出人身伤害、侮辱诽谤刑事案件,正是这一立法缺失的反映。
案例中的两个受害者也曾因“捉奸”的行为受与张某同居的C女的自诉控告,其中王女士未被定罪,而C女的丈夫则经法院审理认定有罪。可见“捉奸”取证难具合法性、有效性,且存有诸多可能导致他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弊端。在当事人以自助方式捉“奸”取证不足取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无过错方取证难的问题呢?笔者注意到对同样可由受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另一事由,即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新婚姻法在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中,为受害人安排了另一救助措施,即“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会、村了委员会应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这里公安机关制止的过程当然包括对暴力行为的“调查取证”的过程。据止笔者认为在法律上同样为受“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所害的一方当事人设置这一求助措施,不失为解决这一事由下无过错方取证难的可予考虑的办法。具体理由如下:
1、此救助措施能解决现行立法的价值取向可能落空的问题,确保新婚姻法能真正起到惩罚过错方,保护受害方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作用。同时此救助措施能解决需要给予保护的无过错方当事人,在调查取证上求助不能的难题,避免当事人以自助的方式取证可能引发的其他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2、诚然,公共权力过多介入公民的私生活领域有许多弊端,轻意不应为之。但当现行立法价值取向的实现又确实需要公共权力为保障时,就应当正确地估量公共权力介入此领域的得与失。从确保现行立法对某一时期社会关系调整的有效性,维护法的权威性、可行性角度出发,此救助措施的设置应该说是“得”大与“失”。
3、尽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属于私生活领域,但此行为与家庭暴力行为 一样,反映出行为人对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法律禁止性规范的违背。基于这样的定性,在受害人的请求下,公共权力的介入与限制公共权力的“人权”理论并不相悖。
4、同样属于私生活领域,同样是为实现立法价值取向之所需,对制止家庭暴力行为设置了这一救助措施,那么对制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设置这一措施,在法理上没有障碍。
(二)关于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认定。
在夫妻一方与婚外异性存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无过错方要获得损害赔偿,依据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必需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过错方与婚外异性已构成 “同居”。这里所指“同居”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解释为系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尽管有此解释,但在个案中仍存在对“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何界定的问题。案例中,用以支持王女士向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主要证据,是公安机关查处张某时,张某自认与婚外某异性在被查处共同居住了一个多月。面对这一证据一、二审法院就该两人是否构成“同居”,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两审法院认定出现的差异正是对何谓“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不同的理解所致。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有误。
首先,笔者赞成一位参与《解释》起草工作的法官所持的如下观点,即“在认定构成同居关系时,应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等方面进行把握”。①这里所指的“双方关系”,显然既包括双方的同居关系,又包括双方在同居前存有的不正当关系。因为双方在同居前存有不正当关系是发展到双方同居的基础。而这种不正当关系的稳定程度如何,可用以判断双方对后来的同居是否持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主观追求。

